乡村分类治理的价值重构与制度创新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Rural Classified Governance
-
摘要: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背景下,村庄分类作为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与空间治理的重要技术工具,已然成为新时代乡村规划研究的焦点议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确立的“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 4类村庄发展导向,本质上是对乡村多元价值体系的政策响应。这种分类治理模式既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理性,更承载着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意图。其不仅是空间治理工具的创新,更是重构新型城乡关系的制度设计。
乡村空间识别与村庄分类研究的广泛展开已呈现显著的科学价值与技术贡献。学者在自然资源本底评价、产业机会识别、生态承载力测算等领域构建起多维度的技术模型,借助遥感监测、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对乡村物质空间与资源禀赋的精准解析。这种基于技术理性的研究路径,有效突破了传统乡村认知的经验主义局限,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可量化、可验证的科学支撑。特别是在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于城乡网络关系的开发识别等方面,技术理性主导的研究方法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
需要警惕的是,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将会催生新的治理悖论。如若村庄分类简化为资源要素的排列组合,发展决策过度依赖数学模型推演,规划学科便陷入了“技术乌托邦”的认知陷阱。在政策实施层面,还面临着“规划—实施”价值断裂的困境:机械套用政策分类标准,将动态演变的乡村系统简化为静态的功能标签;项目投放与资源分配困于技术指标约束,忽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考核评估过度强调量化达标,导致分类治理沦为数字游戏……这些困境暴露出技术理性主导下的制度设计缺陷——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降维成技术规程的执行问题。
更深层的制度症结在于农民主体性地位构建的不充分。现有的村庄分类体系虽在技术层面完善了“物”的评价维度,却容易忽视“人”的发展坐标系。村民群体在规划决策链中的结构性缺席,致使分类治理陷入“主体错位”的困境:一方面,人力资本要素未能纳入资源禀赋评价体系, 使得“乡村振兴”简单等同于“资源振兴”;另一方面,政策实施机制缺乏能力培育维度, 易将“农民主体”虚化为“政策客体”。
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回归乡村规划的价值理性。村庄分类不应是冰冷的技术规程,而应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社会过程。这需要我们重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在技术层面构建“刚性底线+弹性引导”的分类框架,在实施层面针对差异化目标建构差异化路径,在价值层面重塑“村民赋权+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唯有将村民主体力量转化为规划决策的“基础性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从“为乡村规划”到“与乡村共谋”的范式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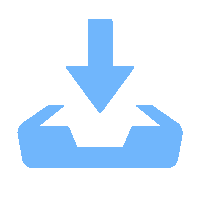 下载:
下载: